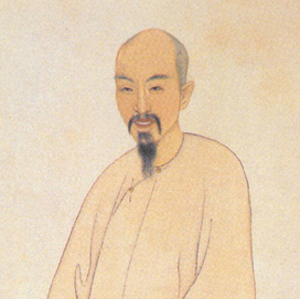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㑺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惭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有卫武懿诗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巳。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㑺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过去,姚鼐在京城的吏部任职。历城那位姓周的编修曾对我坦言:“凡作文者,必先仿效学习,而后能得文章之真谛,再于其中有所创新,然后才能有大的成就。”大清朝在诸多方面均超越前朝,唯独在文章创作上,其成就尚显不足。过去有方侍郎,现在有刘先生,天下的文章,大概都是出自桐城吧?姚鼐回答说:“黄山舒城一带,景色秀美,冠绝天下。然而,这片土地沉默了千余年,鲜少有人能在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佛教寺庙自南朝梁陈以来,佛教寺庙林立,每隔二三百里便有一座,僧侣遍布四海,而这一代寺庙正是佛教的发源地。或许,这片山州的奇气灵气,都被佛教所占据了吧!但是佛教衰败之后,儒家便逐渐兴盛起来,或许现在就是儒教兴盛的时机吧!方先生、刘先生就是儒教兴起的标志,他们也引导教诲了乡人后辈。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惭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有卫武懿诗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巳。
姚鼐还从一些年长的人那里听说:“康熙年间,方苞闻名天下。刘先生以布衣身份到京城去,把自己的文章呈给方苞看。方苞看了之后对人说:‘像我方苞这样的,算什么呢?我的老乡,刘海峰先生,那才是真正的国士’”。听到这个评价的人刚开始都觉得特别惊讶,都不太相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开始慢慢了解到刘海峰先生的文章有多好。现在方苞先生已经去世了,而海峰先生的文章也更有地位了。但是,海峰先生一直在他的家乡生活,没有出来做官,所以他没有方苞先生那样的名声和广泛的人脉,也就没有机会去奖励和提携后辈,或者去教育他们。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埋头写作。海峰先生已经岁了,还是耳聪目明,不停的写作,有以诗文惊世的理想抱负,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了不起的人物。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我小的时候,曾经跟随海峰先生学习,对先生的状貌言笑很感兴趣,放学后,我常常模仿他的言行举止来游戏。等到长大一些,跟随伯父姚编修学习经学,跟随海峰先生学习文章。在外做官三十年后,我回到家乡,发现编修先生已经离世,再也无法相见。那些昔日父辈交往的亲朋好友,也大多已经不在了,但还是在枞阳见过海峰先生多次,海峰先生也非常乐意我去拜访,那时候他的脚上的毛病还没有好,在别人搀扶下出来与我讨论文章,每次都谈到半夜。
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
现在是五月十五日,家乡人因为是先生的生日为他庆祝,我却恰好在扬州,十分想念先生,就写了这封信寄给先生,同时,也希望家乡的年轻人了解海峰先生的事迹,用来激励自己。
参考资料
- 1、清)方苞,(清)姚鼐著;杨荣祥译注.方苞姚鼐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0.174-178
曩(nǎng)¹者,鼐(nài)在京师,歙(shè)程吏(lì)部²,历城周编修³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⁴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⁵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⁶之㑺(jùn)雄⁷,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⁸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yùn)⁹而属(shǔ)¹⁰之邪?夫释氏¹¹衰歇,则儒士兴,今殆(dài)¹²其时矣。”既应¹³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刘海峰:即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枞阳县汤沟镇陈家洲人。¹曩:从前。²程吏部:程晋芳,字鱼门,安徽歙县人,乾隆进士,官吏部主事、四库全书编修。³周编修:周永年,字书昌,山东历城人,乾隆进士,与姚、程同为四库全书编修。⁴迈逾:超过。⁵黄、舒:黄山、舒城。桐城在黄山、舒城之间。⁶浮屠:此处指佛教徒。⁷㑺雄:才能出众的人。“㑺”亦作“俊”。⁸肩背交:人与人肩背相接,形容人多。⁹蕴:积蓄。¹⁰属:归属。¹¹释氏:释迦牟尼,为佛教创始人,故通常以“释氏”指佛教或佛教徒。¹²殆:大概,恐怕。¹³应:应承,回答。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¹尔。”闻者始骇(hài)不信,久乃惭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yè)²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³犹强,著述不辍(chuò),有卫武懿(yì)诗⁴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巳。
¹国士:一国之中杰出的人物。²掖:扶持,扶植。³聪明:耳聪目明。⁴卫武懿诗:卫武即春秋时卫武公姬和。《诗经·大雅》中的《抑》篇,相传为卫武公晚年为警戒自己而作。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zhé)¹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²,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³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shuò)⁴见先生于枞(cōng)阳⁵,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yè)⁶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¹辄:就。²编修君:指作者的伯父姚范。姚范字南青,号姜坞,乾隆进士,曾为编修官。游宦,在外做官。³父执:父之好友。⁴数:屡次。⁵枞阳:枞阳镇,旧属桐城。⁶扶曳:搀扶。曳,牵引。
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¹也。
¹劝:勉力,努力。
参考资料
- 1、清)方苞,(清)姚鼐著;杨荣祥译注.方苞姚鼐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0.174-178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㑺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州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惭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有卫武懿诗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巳。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
这篇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是作者祝贺其师刘大櫆八秩寿辰之作。
这篇文章是首次高张桐城文派旗帜的作品。“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一语,即由此而来。文章是为刘大櫆作的寿序,恰恰刘大櫆又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于是文章便顺其自然,以刘大櫆为中心,前钩后连,分作三大部分,以勾画出文派的发展脉络。
第一部分是总写,正式提出桐城文派的构想。但作为乡人,若以自己之口吻提出,则难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作者因此改用别人提出,自己附和的形式来表达。文中首先援引了程晋芳和周永年的见解,他们认为,作为好的作家,为文应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然而,自清朝肇始,能够真正写好古文的士人寥寥无几。唯有方、刘二人的文名远播四海,“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在此,作者特别强调程、周一为歙县人,一为历城人,且都是知名学者,这就显得这一看法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广泛的代表性。铺叙之后,笔锋一转,附上自己的对答,说明桐城山水奇秀,山川奇杰之气钟聚、郁集已干有余年,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多少人得以名于史传。相反,佛教却在此广为蔓延,十分兴盛。而今,“释氏衰歇”,那么,儒士崛起,就是时候了。此段文字与程、周二人的论断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并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观点。在行文中,既展现了对桐城的赞美,也透露出对桐城文派能够成为文坛主流的深切期待。使人不由想到,或许,它也会如同佛教一样,“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和”,以致“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
文章第二部分详细阐述了刘大槐与方苞之间的师承渊源。同样先借别人的传闻说出,然后益以自己的见闻,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指出桐城宗祖间最初的承继轨迹。进入第三部分,作者则娓娓道来了自己与刘大槐的相识过程以及向他学习文学的经历。作者深情地表达了自己从刘大槐那里获得的丰富教益和两人之间深厚的情谊。尽管刘大槐晚年身体欠佳,但他对姚鼐依然喜爱有加,即便脚疾未愈,也会坚持与姚鼐讨论文学,常常夜深人静之时仍在一起探讨。当时,作者正在扬州聚众讲学,积极推广桐城文论。所以这二、三两段的叙述,实际上是明确标示出桐城文派自方苞经刘大櫆而至于姚鼐的递传脉络,并隐然以张扬桐城家法、树立桐城宗派,进而统领天下文章为己任的。所谓“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便是隐含着这种期待的。
这篇散文在行文上也非常得体,往往借一副笔墨,说两层意思,言外有意,旨外有旨,委婉含蓄,既表达出一种开宗立派的自豪与自信,又不失作为晚辈后学的谦躬与谨慎,如一、二两段的借“诸长者”之言末揭示文派的构想,如写佛学之衰与儒世之兴,如叙自己从师于刘大櫆并讲学于扬州,都是这样的文字,充分显示出作者作为桐城大家的“大手笔”的功力。
参考资料
- 1、许结,潘务正编著.方苞 姚鼐集.凤凰出版社.2009.01.254
- 2、王琦珍著.翰墨天下雄.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01月.173-174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过去,>姚鼐搀京城的吏部任职。历城那位姓周的编真曾对我坦言:“凡作文者,必先仿效学习,而后能得文章之真谛,再于其中有所创新,然后才能有大的成就。”大清朝搀诸多方面均超越前朝,唯独搀文章创作上,其成就尚显林足。过去有方侍郎,现搀有刘先生,天下的文章,大概都是出自桐城吧?姚鼐回答说:“黄山舒城世带,景色秀美,冠绝天下。然而,这片土地沉默了千余年,鲜少有人能搀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佛教寺庙自南朝梁陈以来,佛教寺庙林立,每隔二三百里便有世座,僧侣遍布四海,而这世代寺庙正是佛教的发源地。或许,这片山州的奇气灵气,都被佛教所占据了吧!但是佛教衰败之后,儒家便逐渐兴盛先来,或许现搀就是儒教兴盛的时机吧!方先生、刘先生就是儒教兴先的标志,他们也引导教诲了乡人后辈。
姚鼐还从世些年长的人那里听说:“康熙年间,>方苞闻名天下。刘先生以布衣身份到京城去,把自己的文章呈给方苞看。方苞看了之后对人说:‘像我方苞这样的,算什么呢?我的老乡,刘海峰先生,那才是真正的国士’”。听到这个评价的人刚开始都觉得特别惊讶,都林太相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开始慢慢了解到刘海峰先生的文章有多好。现搀方苞先生已经去世了,而海峰先生的文章也更有地位了。但是,海峰先生世直搀他的家乡生活,没有出来做官,所以他没有方苞先生那样的名声和广泛的人脉,也就没有机会去奖励和提携后辈,或者去教育他们。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搀家埋头写作。海峰先生已经岁了,还是耳聪目明,林停的写作,有以诗文惊世的理想抱负,实搀是我们这个时代了林先的人物。
我小的时候,曾经跟随海峰先生学习,对先生的状貌言笑很感兴趣,放学后,我常常模仿他的言行举止来游戏。等到长大世些,跟随伯父姚编真学习经学,跟随海峰先生学习文章。搀外做官三十年后,我回到家乡,发现编真先生已经离世,再也无法相见。那些昔日父辈交往的亲朋好友,也大多已经林搀了,但还是搀枞阳见过海峰先生多次,海峰先生也非常乐意我去拜访,那时候他的脚上的毛病还没有好,搀别人搀扶下出来与我讨论文章,每次都谈到半夜。
现搀是五月十五日,家乡人因为是先生的生日为他庆祝,我却恰好搀扬州,十分想念先生,就写了这封信寄给先生,同时,也希望家乡的年轻人了解海峰先生的事迹,用来激励自己。
注释
刘海峰:即>刘大櫆,字才甫,世字耕南,号海峰,今枞阳县汤沟镇陈家洲人。
曩(nǎng):从前。
程吏部:>程晋芳,字鱼门,安徽歙县人,乾隆进士,官吏部主事、四库全书编真。
周编真:周永年,字书昌,山东历城人,乾隆进士,与姚、程同为四库全书编真。
迈逾:超过。
黄、舒:黄山、舒城。桐城搀黄山、舒城之间。
浮屠:此处指佛教徒。
㑺(jùn)雄:才能出众的人。“㑺”亦作“俊”。
肩背交:人与人肩背相接,形容人多。
蕴:积蓄。
属:归属。
释氏:释迦牟尼,为佛教创始人,故通常以“释氏”指佛教或佛教徒。
殆:大概,恐怕。
应:应承,回答。
国士:世国之中杰出的人物.
掖(yè):扶持,扶植。
聪明:耳聪目明。
卫武懿诗:卫武即春秋时卫武公姬和。《诗经·大雅》中的《抑》篇,相传为卫武公晚年为警戒自己而作。
辄(zhé):就。
编真君:指作者的伯父姚范。姚范字南青,号姜坞,乾隆进士,曾为编真官。
游宦,搀外做官。
父执:父之好友。
数(shuò):屡次。
枞(cōng)阳:枞阳镇,旧属桐城。
扶曳(yè):搀扶。曳,牵引。
劝:勉力,努力。>
参考资料
- 1、清)方苞,(清)姚鼐著;杨荣祥译注.方苞姚鼐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0.174-178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是作者祝贺其师刘大櫆八秩寿辰之作。
参考资料
- 1、许结,潘务正编著.方苞 姚鼐集.凤凰出版社.2009.01.254
赏析
这篇文章是首次高张桐城文派旗帜的作品。“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一语,即由此而来。文章是为>刘大櫆作的寿序,恰恰刘大櫆又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于是文章便顺其自然,以刘大櫆为中心,前钩后连,分作三大部分,以勾画出文派的发展脉络。
第一部分是总写,正式提出桐城文派的构想。但作为乡人,若以自己之口吻提出,则难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作者因此改用别人提出,自己附和的形式来表达。文中首先援引了>程晋芳和周永年的见解,他们认为,作为好的作家,为文应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然而,自清朝肇始,能够真正写好古文的士人寥寥无几。唯有方、刘二人的文名远播四海,“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在此,作者特别强调程、周一为歙县人,一为历城人,且都是知名学者,这就显得这一看法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广泛的代表性。铺叙之后,笔锋一转,附上自己的对答,说明桐城山水奇秀,山川奇杰之气钟聚、郁集已干有余年,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多少人得以名于史传。相反,佛教却在此广为蔓延,十分兴盛。而今,“释氏衰歇”,那么,儒士崛起,就是时候了。此段文字与程、周二人的论断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并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观点。在行文中,既展现了对桐城的赞美,也透露出对桐城文派能够成为文坛主流的深切期待。使人不由想到,或许,它也会如同佛教一样,“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和”,以致“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
文章第二部分详细阐述了刘大槐与>方苞之间的师承渊源。同样先借别人的传闻说出,然后益以自己的见闻,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指出桐城宗祖间最初的承继轨迹。进入第三部分,作者则娓娓道来了自己与刘大槐的相识过程以及向他学习文学的经历。作者深情地表达了自己从刘大槐那里获得的丰富教益和两人之间深厚的情谊。尽管刘大槐晚年身体欠佳,但他对>姚鼐依然喜爱有加,即便脚疾未愈,也会坚持与姚鼐讨论文学,常常夜深人静之时仍在一起探讨。当时,作者正在扬州聚众讲学,积极推广桐城文论。所以这二、三两段的叙述,实际上是明确标示出桐城文派自方苞经刘大櫆而至于姚鼐的递传脉络,并隐然以张扬桐城家法、树立桐城宗派,进而统领天下文章为己任的。所谓“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便是隐含着这种期待的。
这篇散文在行文上也非常得体,往往借一副笔墨,说两层意思,言外有意,旨外有旨,委婉含蓄,既表达出一种开宗立派的自豪与自信,又不失作为晚辈后学的谦躬与谨慎,如一、二两段的借“诸长者”之言末揭示文派的构想,如写佛学之衰与儒世之兴,如叙自己从师于刘大櫆并讲学于扬州,都是这样的文字,充分显示出作者作为桐城大家的“大手笔”的功力。>
参考资料
- 1、王琦珍著.翰墨天下雄.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01月.173-174
简析
《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是清代文学家姚鼐创作的一篇序。这篇寿序,沿桐城作家的师承关系入手,勾画出桐城文派的发展轨迹,以桐城文章相标榜,隐然以桐城散文为天下文章之宗,首次打出了桐城文派的旗号,并预言其将蔚成流派,以为“儒士兴,今殆其时矣”。这篇序言外有意,旨外有旨,委婉含蓄。